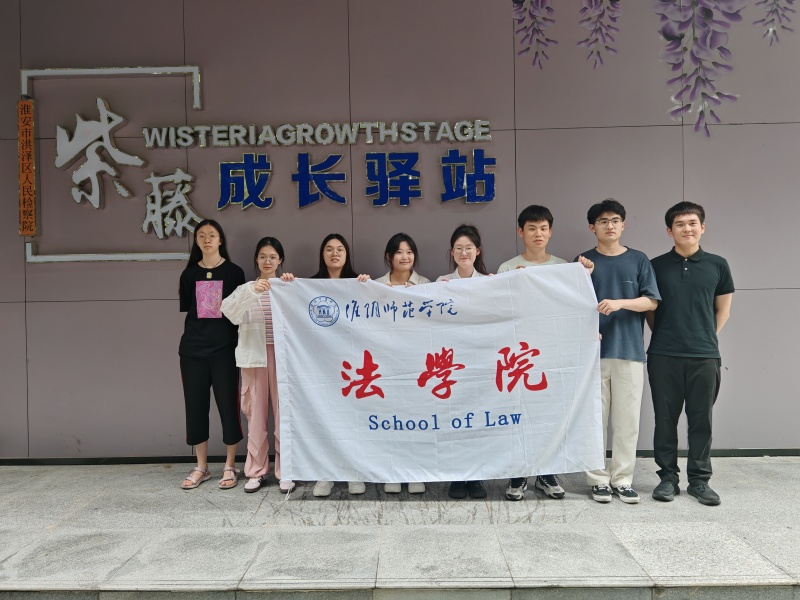文/潘友娟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案情:
朱某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4年结婚,后张某先后于2007、2009、2014年分别因犯盗窃罪、寻衅滋事罪、贩卖毒品罪被判处刑罚,并于2015年4月刑满释放。2017年4月2日,张某从朱某处拿取人民币10万元,驾车至湖北省宜昌市,通过他人购得甲基苯丙胺1800余克,并将上述毒品放置在一个蓝色手提包内。同月4日,张某携带上述手提包驾车返回泰州。途中,张某与朱某联系,约定由朱某至途中接其,后朱某邀请蔡某驾车送其前往。4月5日凌晨,张某、朱某、蔡某三人在安徽省滁州市吴庄(南)服务区会合。后张某要求朱某将蓝色手提包带至蔡某驾驶的轿车上并与蔡某一起返回泰州。到达泰州后,朱某又携带该蓝色手提包至张某驾驶轿车上准备返回家中。因途中张某怀疑有人跟踪,遂要求朱某携带蓝色手提包下车并藏匿。朱某下车后先将该手提包藏匿于路边油菜田中,后步行至九龙大街又搭乘出租车返回藏匿地点将提包取回,并乘车将该提包藏匿于其姨夫家中杂物房内。同日,公安民警抓获张某、朱某,次日,公安民警在朱某家中一卧室桌面扣押甲基苯丙胺一袋,重0.7克,在电视柜下扣押电子秤一台。归案后,朱某对于自己对提包内物品为毒品的主观明知拒不供认。
争议:
“零口供”并非仅指犯罪分子对于犯罪事实始终保持沉默、缄口不言的情况,也包括犯罪分子心存侥幸,只作无罪辩解,拒绝作有罪供述,企图蒙混过关的情形。该类被告人面对司法机关的调查时并非一言不发,而是诸多辩解,供述内容真假交织,编织迷雾,给公诉人对案件事实的过滤和甄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因为其并没有直接参与主犯罪事实的实行行为,因此认定其对毒品的主观认知直接影响其是否构罪以及构成何罪。回到本案之中,被告人朱某即系该种情形。归案后其对于案发当晚的行动过程无异议,但对于蓝色手提包内物品的性质不予认可,供述时避重就轻、闪烁其词,如其辨称张某从其处拿取10万元是为了回老家祭祖、因担心丈夫的安全与丈夫约定在安徽碰面,帮助丈夫藏匿提包是因为害怕丈夫的责骂、自己不吸毒不知道毒品的常识等等,而同案犯朱某的丈夫张某虽然认可自身的犯罪事实,但其对于是否事前与朱某商议、是否告知朱某其去湖北的目的、在路途上是否谈论到毒品的有关事宜均予以了否认。全案无直接证据证实朱某的主观明知,因此在本案起诉之前,一共形成三种争议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朱某对于蓝色手提包内物品系毒品的主观认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对其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
一种观点认为朱某对于毒品性质的认知的时间点应为其丈夫张某让其拿着提包下车藏匿时,因此认定其构成窝藏、转移毒品罪。
一种观点认为朱某与丈夫张某在安徽汇合时就应当认知到事情发展的不正常之处,其对于毒品的认知在运输途中就已经形成,应认定其构成运输毒品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认定:
在直接证据缺位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毒品零口供案件,重点还在于如何审查运用间接证据,特别是帮助犯,在其帮助行为与犯罪实行行为分离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一种“外围包围中心”的证明模式,
一、着重审查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关联
毒品共同犯罪中,最外围的基础事实应当是共同犯罪人之间的交往情况。帮助犯虽然未参与核心犯罪事实,但是其参与到犯罪之中一定是基于其与正犯之间存在联系。回到本案,朱某和张某系夫妻关系,2004年两人结婚之后,双方共同生活,朱某对于张某的性格和行事特征有一定的了解。张某多次犯罪入狱,其于2015年出狱之后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收入来源,而且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结合张某此前多次入狱的经历,当张某从朱某处拿取了10万元时,朱某对于10万元的用处自然会产生怀疑。再来看朱某的辩解,其辩称张某的老家在湖北宜昌,张某告知其10万元是为了清明节回家祭祖,案发时间确实在2017年清明节期间,因此张某的辩解得到了部分的印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基础事实,朱某可以推断出张某该次去湖北存在可疑之处,张某存在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但并不能直接推断出张某一定会实施犯罪。
二、着重审查行为人对毒品犯罪的认知程度
在建立了行为人对主犯行为的初步判断之后,向前更进一步的基础事实是行为人对毒品的认知程度。毒品犯罪中的帮助犯普遍辩解是对毒品犯罪并不了解,大多数会称自己仅仅是出于亲戚、朋友之间的帮忙,单纯地按照主犯的安排实施行为,对于其他事情并不过问等等,如果再加之行为人没有吸毒经历、未受过涉毒处罚,那么认定其对毒品的认识确实存在一定的障碍。但行为人之间的关联告诉我们,共同犯罪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不会没有犯罪的蛛丝马迹,我们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在案卷中找线索,把线索串联成绳索,紧紧捆绑住行为人。
回到本案之中,朱某之前并未受过刑事、行政处罚,没有吸毒恶习,也具有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仿佛其与毒品犯罪之间确实不相干,但是再次细看案件证据却不难发现,朱某作为丈夫张某人生经历的旁观者,对于毒品犯罪的了解并非是一张白纸。首先,丈夫张某曾经因为贩卖毒品被判处过刑罚,该犯罪事实发生在二人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其次,在朱某和张某共同生活的家中,侦查机关扣押到了一包重约0.7克毒品,并且在电视柜下发现了电子秤;再次,张某并无固定工作,也无稳定收入,其如何保证自己的生活开支?
这些疑点单独来看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可能没有帮助,但是结合在一起,已经充分证明朱某对毒品的认知程度已经远远高于普通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其再辩解自己对于毒品毫不了解、辩解丈夫张某与毒品毫无关联也就显得无力了。
三、着重审查共同犯罪人在毒品犯罪中的客观行为
外围基础事实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支撑中心推定事实,但是仅仅依靠外围基础事实显然还不能直接推定出中心事实,此时还需要办案人员回归到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上,找到行为人至关重要的关键行为,卡住犯罪分子的喉咙,让其无处可逃。
回到本案之中,朱某与张某联系之后在安徽回合,根据张某供述,为了防止检查张某将毒品留在自己车上,将蓝色手提包交给朱某,并要求朱某搭乘蔡某的汽车返回,在回程途中双方不断电话联系,张某询问朱某是否遇到检查,结合前述的两个基础事实,朱某应当认识到当晚事情的不正常之处,但是到此时为止,朱某还没有接触到毒品,因此还不能武断地推定朱某已经知道张某当晚的行为涉及到毒品。但到达泰州之后,朱某与张某同乘一辆车准备返回家中,并且实施了本案中最关键的一个行为,即张某要求朱某携带蓝色手提包下车藏匿,此时朱某才实际真切地接触到了毒品,虽然其一直辩解没有打开手提包查看,但试想在凌晨的荒郊野外,丈夫将妻子和一个手提包赶下车,指使其将提包藏好,结合之前张某的犯罪经历、从家中拿取的10万元钱、路上不断查问是否有检查,朱某应当怀疑包中的物品,再加上之后朱某又继续实施了一个对自己主观明知予以强化的行为,即其在将毒品藏匿到菜花田内后并没有彻底离开,而是步行一段距离后又打车返回取回了物品,并且没有带回家中,而是选择藏匿在其亲属家中,上述客观行为一步接一步、一环套一环,逐步加强朱某对于包内物品的性质是毒品的主观认知,并且最终得出其明知提包内是毒品而帮助转移、藏匿的推定事实。综上,应当从朱某携带提包下车时开始评价为朱某的犯罪行为,并以窝藏、转移毒品罪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一、二审法院均判处朱某犯窝藏、转移毒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