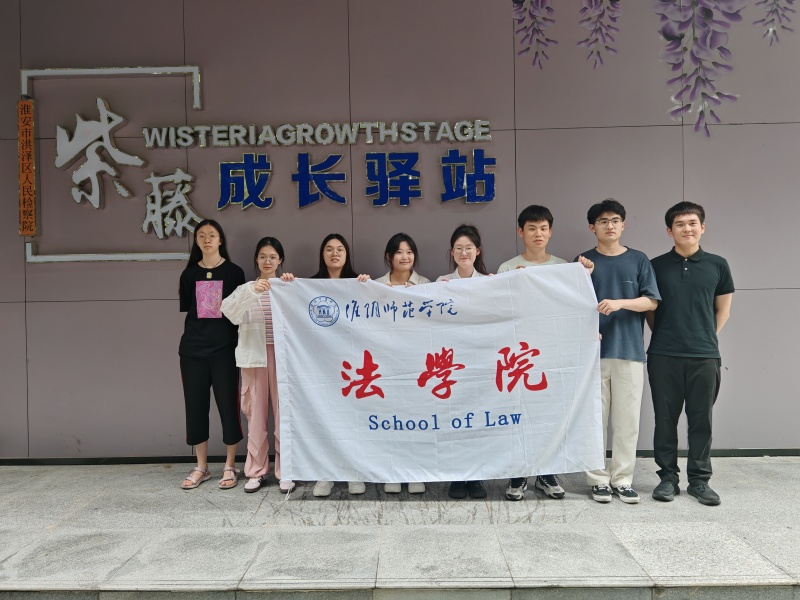老舍先生通过茶馆这样一个人流复杂的地方,不仅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还成功的塑造了众多人物,通过他们在茶馆的一言一行来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人们思想的腐朽性。
王利发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在书中,他巧于应付巡警的敲诈,耐心倾听崔久峰的牢骚。作为商人,他还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如他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处境和难民的哀告虽然有同情,但也很有限度。他对社会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的十分含蓄,如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这句话中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在那个没有人敢说真话的时代,王利发的语言就由个性化的点延伸到了面。就如王利发这一人物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人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王利发的视角是和普罗大众做着广泛的接触,官僚权贵,地痞流氓,外国势力,警察特务不停地对他敲诈滋扰,他选择了忍让,选择了一个老实巴交的顺民形象。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王利发进行了多次改革,而这些无尽的妥协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其盘剥和讹诈直至一穷二白的无情现实。被生活逼上了绝路的王利发终于喊出了多年未曾敢喊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办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我可没做过缺德事儿啊,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就是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将那些为了生计奔走却一场空的小商人的心声喊了出来。
作者对王利发的命运际遇只能报以深深的同情和无奈,一个最不该自灭的生命,一个苟延残喘的生命,一个琐碎的生命的消逝,就是当时普罗大众的集中代表。
秦二爷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完全可以靠着祖上的财产,吃喝玩乐一辈子,但是面对国弱民穷,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他决心搞实业救国。变卖了家里所有的房产、地产,办了个“顶大顶大”的工厂,但是,在那个黑暗的、腐朽的时代,他的努力最终只能化成泡影。当他从自己亲手办的工厂被赶出来时,只带了签支票用的金笔和在工厂门口捡到的两个螺丝帽。他对王利发说:“人哪,有钱就该吃喝嫖赌,决不能做好事,做好事绝没有好下场!”他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靠实业救国是行不通的,秦仲义对祖国的热情与最后的无奈绝望,都是当时想靠实业救国的一批爱国人士所共有的,老舍先生通过一个秦仲义也反映了实业救国人士们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也将矛头指向了那罪过的时代。点与面的交织也很明显了。
常四爷是个旗人,但他对腐朽的清朝政府不满,对帝国主义更加痛恨。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书中他对抓过他的特务不服软,为正发愁的王利发送来了咸菜和鸡。他的身上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爱国精神。
作者也通过常四爷与松二爷两个旗人形象的对比,既写出了当时一类好闲懒做的旗人形象,同时又刻画了旗人下层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形象。常四爷的命运也逃不出历史的窠臼,老年的常四爷一身清贫,感慨道,“我爱我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啊?”一声呐喊喊出了爱国的旗人们的悲剧命运,喊出了他们的无奈与愤慨。
刘麻子,这是一个靠做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书中他同两位逃兵谈生意,还没有谈成就被当做逃兵枪毙了。作者以刘麻子为典型,揭示了当时下层人民为了生计,出卖灵魂的生活状况,同时也表现出当时社会的病态与畸形。
老舍先生通过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刻画来表现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社会病态中。这些人物,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国家和生活有着不同的感悟,作者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做具体分析,就将面聚焦到点,再由点聚散开来,形成了点到面,再由面到点的延伸。
茶馆是一个小社会,通过一个小小的茶馆,将社会百态聚集于此,茶馆中的人与事都是点,但反应了是社会这个面。由此,点与面的交织就体现出来了。(新沂市检察院 仲康)